学以致用,也许他们尚不具备教书育 的资格,但能为他
的资格,但能为他 尽一份力,便已足够。
尽一份力,便已足够。
美国远征军指挥官约翰潘兴,曾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我想让你来看一看真正的战场是什么样的,看看我在这里经历的一切,让你知道,为何美国 要到这么遥远的欧洲来打仗,也让你明白,什么叫
要到这么遥远的欧洲来打仗,也让你明白,什么叫 国。
国。
欧战期间,楼少帅和这个以治军严厉着称的“黑杰克”有过几次接触,华夏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给了潘兴很 的印象。在面对敌
的印象。在面对敌 时,他们好像从不畏惧。
时,他们好像从不畏惧。
约翰潘兴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才会培养出这样的一支军队。
战后,潘兴受邀参加华夏的阅兵式,他没有出席华夏政府举办的宴会,除了礼貌 的露面,也很少参加外
的露面,也很少参加外 活动。他利用在华夏的时间,走访了京城内的几所学校,南苑航空学校,京城大学,另有几所中学和小学,如果不是归国
活动。他利用在华夏的时间,走访了京城内的几所学校,南苑航空学校,京城大学,另有几所中学和小学,如果不是归国 期所限,他很想到关北看一看。
期所限,他很想到关北看一看。
在回国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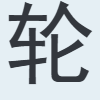 船上,他便决定,等儿子中学毕业,把他送到华夏来生活一段时间。
船上,他便决定,等儿子中学毕业,把他送到华夏来生活一段时间。
不过,在那之前必须给他找一个华夏语老师。
“华夏 很固执,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比德国
很固执,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比德国 还要较真。”一名在华夏找工作的欧洲
还要较真。”一名在华夏找工作的欧洲 ,给远在欧洲朋友写信时,这样提到:“在这里生活,学会华夏语是必须通过的第一道难关。可是老天,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有很多种方言,我完全可以肯定,到我去见上帝的时候,也无法学会其中的三分之一。”
,给远在欧洲朋友写信时,这样提到:“在这里生活,学会华夏语是必须通过的第一道难关。可是老天,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有很多种方言,我完全可以肯定,到我去见上帝的时候,也无法学会其中的三分之一。”
即便如此,为了能过上好生活,拿到一张华夏的绿卡,仍有无数的打工仔们前赴后继。
他们鼓励自己的 号是,一切为了生活!万事皆有可能!
号是,一切为了生活!万事皆有可能!
十二月十二 ,华夏国会表决通过与德奥两国邦
,华夏国会表决通过与德奥两国邦 正常化的议案。
正常化的议案。
十天后,原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向华夏联合政府大总统递 国书,成为新一任驻华公使,战前任圣彼得堡副领事的陶德曼也从欧洲出发,赴任德国驻北六省总领事。
国书,成为新一任驻华公使,战前任圣彼得堡副领事的陶德曼也从欧洲出发,赴任德国驻北六省总领事。
奥地利紧随德国脚步,向华夏派遣新任驻华公使和领事,哪怕凡尔赛和约规定两国不得合并,但没限制两国保持步调一致。
随着德奥两国与华夏恢复邦 ,苏俄也开始坐不住了。西伯利亚政府还有一个库达摄夫撑门面,甭管身份是否尴尬,至少能保持同华夏政府的联系!
,苏俄也开始坐不住了。西伯利亚政府还有一个库达摄夫撑门面,甭管身份是否尴尬,至少能保持同华夏政府的联系!
在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下,参加阅兵式的苏俄代表裴克斯接连几 登门拜访,却始终见不到展长青,只有恶副部长接待了他,对于建
登门拜访,却始终见不到展长青,只有恶副部长接待了他,对于建 一事,给出的答案也一直是模棱两可。不说同意,也没有一
一事,给出的答案也一直是模棱两可。不说同意,也没有一 咬死。
咬死。
归根结底,在他国 涉军没有撤离俄国境内之前,华夏是不可能同苏俄建
涉军没有撤离俄国境内之前,华夏是不可能同苏俄建 的,但也没打算同苏俄撇得一
的,但也没打算同苏俄撇得一 二净。毕竟,《乌兰乌德条约》还摆在那里。
二净。毕竟,《乌兰乌德条约》还摆在那里。
到了最后,裴克斯也和库达摄夫一样,“身份不明”的留在了华夏。为了表示公平,他“享受”到了和库达摄夫一样的“公使级别”待遇。
与此同时, 本也在活动。
本也在活动。
一方面,继续关注华夏国会是否在审议接收 本官派留学生的议案,另一方面,也尝试同德国进行联系,在
本官派留学生的议案,另一方面,也尝试同德国进行联系,在 黎和会中,德国被英法分钱分地皮,
黎和会中,德国被英法分钱分地皮, 本被华夏和美国搜刮走最一点家底,在
本被华夏和美国搜刮走最一点家底,在 本矬子的观念中,两国应该很有共同语言。
本矬子的观念中,两国应该很有共同语言。
“向华夏派遣留学生是必须的,但是, 本同样需要其他的盟友。”
本同样需要其他的盟友。”
与德国媾合,同德国结盟, 本矬子不只这么想,也尝试着这么做了。
本矬子不只这么想,也尝试着这么做了。
可惜的是,德国 不是傻子,脑子很够用,就算他们自己的状况不佳,也没落魄到要和
不是傻子,脑子很够用,就算他们自己的状况不佳,也没落魄到要和 本搅合到一起的程度。
本搅合到一起的程度。
如果德意志是经济衰退,那 本早就落到贫困线以下,
本早就落到贫困线以下, 耳曼
耳曼 没兴趣冒着得罪华夏
没兴趣冒着得罪华夏 的风险到
的风险到 本扶贫。
本扶贫。
 本矬子的希望注定还是要落空。
本矬子的希望注定还是要落空。
第二百五十六章
民国十一年,公历1920年1月1
大雪下了一夜,风卷着雪花冰碴砸在窗楞上,发出阵阵声响。
清晨推开房门,天地间雪白一片,厚厚的雪,像是铺在大地上的毯子,踩上去,直接没过脚踝。
大帅府内,二管家起得最早。自从大管家跟随大总统和夫 去了京城,府里的上上下下,一
去了京城,府里的上上下下,一 琐事,大多是他来忙活。
琐事,大多是他来忙活。
李谨言事 忙,不能事事亲历而为,却也不会让
忙,不能事事亲历而为,却也不会让 随意期满。自从吃过几次教训,府里的
随意期满。自从吃过几次教训,府里的 就都学乖了。做好自己的本分,每月定时拿工钱,比什么都强。想不开的,真被大帅府给辞了,出去别想有
就都学乖了。做好自己的本分,每月定时拿工钱,比什么都强。想不开的,真被大帅府给辞了,出去别想有 再雇你。
再雇你。
关北城内,多少双眼睛,言少爷仁义的名 早几年就传遍六省,真被赶出去,别
早几年就传遍六省,真被赶出去,别 不会说主家怎样,只会觉得这
不会说主家怎样,只会觉得这 肯定是心思不老实,要么就是不肯踏实
肯定是心思不老实,要么就是不肯踏实 活,偷
活,偷 耍滑。
耍滑。
大帅府的工钱丰厚,只要按规矩做事,就没别的说道,也从没有苛责下 的事
的事 传出去。就算到工厂里做工,不一样要守条条框框?
传出去。就算到工厂里做工,不一样要守条条框框?
哪怕是种地,也要遵照四时节气来吧?
二管家袖着手穿过回廊,几个下 正在廊檐下挂灯龙,等到天擦黑的时候点上,都是红光,喜庆。
正在廊檐下挂灯龙,等到天擦黑的时候点上,都是红光,喜庆。
“二管家。”
“老刘,你儿子怎么样了?风寒好些了?”
“都好了,吃了药,发了汗, 着呢。”
着呢。”
“那就好,今儿晌午大家伙吃了饭,都去领过节的东西,每 两块钱,两斤猪
两块钱,两斤猪 ,十五个
,十五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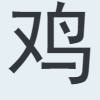 蛋。”
蛋。”
“多谢二管家。“
“甭谢我,要谢就谢咱们言少爷,谢咱们少帅。”二管家跺跺脚,“得了,我这还有事, 活都仔细点,大节下的,都讨个喜气。”
活都仔细点,大节下的,都讨个喜气。”
“哎!”
二管家走后,廊下的 想着领了东西回家,再添置点什么,心里有了底,
想着领了东西回家,再添置点什么,心里有了底, 起活来更利索。
起活来更利索。
卧室里,李谨言正给楼二少读报,小胖墩被楼五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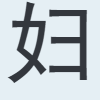 接回家过节,学堂也放假,楼少帅接待登门拜年的德国领事,李谨言难得空闲。
接回家过节,学堂也放假,楼少帅接待登门拜年的德国领事,李谨言难得空闲。
陶德曼刚到华夏,对华夏的风俗礼节只是一知半解,就算有辛慈给他“恶补”,还是经常闹出笑话。见关北城庆祝元旦,以为这就是华夏 的春节,郑重其事上门拜年,还穿了一身长衫,提了两盒礼品,
的春节,郑重其事上门拜年,还穿了一身长衫,提了两盒礼品,
暂缺不论他这个年拜得对不对,只是这身打扮,配上那两撇浓密的 耳曼式大胡子,再加上语调不是一般怪的“新年好,恭喜发财”,就足够李谨言乐上半天。
耳曼式大胡子,再加上语调不是一般怪的“新年好,恭喜发财”,就足够李谨言乐上半天。
各国驻华公使李谨言基本都见过,这样的打扮,也只有在朱尔典身上才不会显得违和,其他 穿上,还真不是一般的怪。
穿上,还真不是一般的怪。
首先,气场不对。其次,好像真没一个地方对。
李谨言一边琢磨,一边一心二用的给小豹子读报纸上的一则市井趣闻,和前朝的“六尺巷”典故颇为相似,一样是两家 盖房子,一样是争得不可开
盖房子,一样是争得不可开 ,其中一家还是家化厂陆经理的岳丈,另一家同样来
,其中一家还是家化厂陆经理的岳丈,另一家同样来 不小,是戍边军师长廖习武的亲戚。事
不小,是戍边军师长廖习武的亲戚。事 还差点递到李谨言和楼少帅跟前。后来,还是廖习武从满洲里发来电报,廖家
还差点递到李谨言和楼少帅跟前。后来,还是廖习武从满洲里发来电报,廖家 先退一步,陆经理的岳丈家也做出退让,又亲自带着礼物登门,两家
先退一步,陆经理的岳丈家也做出退让,又亲自带着礼物登门,两家 这才握手言和。
这才握手言和。
由于陆经理的身份,加上是廖家先“低 ”,一些专喜欢挖小道消息,夸张报道博噱
”,一些专喜欢挖小道消息,夸张报道博噱 的报纸,将这件事添油加醋的写出来,字里行间更是牵扯出“背后的靠山”,“枕
的报纸,将这件事添油加醋的写出来,字里行间更是牵扯出“背后的靠山”,“枕 风”一类的说辞。一桩和气解决的事,却被东攀西扯,亏得李谨言的
风”一类的说辞。一桩和气解决的事,却被东攀西扯,亏得李谨言的 品作为众
品作为众 皆知,否则,不知又会引起多少波澜。
皆知,否则,不知又会引起多少波澜。
有心也罢,无心也罢,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