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便居民膜拜,纪念他对地方的德政。等势利小 吕惠卿得势之后,他设法弄到一
吕惠卿得势之后,他设法弄到一
纸朝廷命令,将此纪念亭拆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湖中的恶 不再滋生。苏东坡想到一个办法,就是
不再滋生。苏东坡想到一个办法,就是
把沿岸部分开垦出来让农 种菱角。农
种菱角。农 必须注意将自己地段按期除
必须注意将自己地段按期除 。他向中书
。他向中书
省上书,请求确保此项税收,必须应用在湖堤和湖的保养上。
除去增加西湖的实用价值之外,不管是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苏东坡也增加了
西湖的美。但是这种德政后来也遭致政敌的攻击,说他“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
湖中,以事游观”。
苏东坡又试验更庞大的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这是苏州城外一项拖船
驳运计划。还有后来他把在杭州西湖所做的工程也施之于阜阳的西湖。这些计划有
些没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密计划,足以证明他在工程方面的想象力。
我们必须提到他的一项庞大工程计划,不过因为他被召还京未及实现而已。那
个详密计划现今依然保存。在钱塘江 杭州湾的江
杭州湾的江 ,有一个小岛,那个地方每年
,有一个小岛,那个地方每年
船毁 亡,损失惨重。钱塘江势如奔马的洪流正好与流
亡,损失惨重。钱塘江势如奔马的洪流正好与流 海湾来的海水相遇,受阻
海湾来的海水相遇,受阻
于此一小岛,遂变成了极其危险的漩涡逆流。这个“浮山岛”之得名,就因为四周
沙洲时隐时现,而驾船者无从辨认水道何在。这些沙洲有的一二里长,据说一夜的
工夫就会完全失踪不见。旅客乘船到杭州,这一段路最为可怕。自浙江东岸来的 ,
,
宁愿在龙山横过海湾,但是从东南地区顺钱塘江而下的 ,则不得不冒险经过。有
,则不得不冒险经过。有
时可以看见落水的大 儿童哭喊救命,还没来得及抢救,已被洪流巨
儿童哭喊救命,还没来得及抢救,已被洪流巨 吞没。但是
吞没。但是
杭州江上的 通还是很重要。贫苦的西南地区
通还是很重要。贫苦的西南地区 民,都以杭州以北西湖地区产的米
民,都以杭州以北西湖地区产的米
为生,而杭州 则依赖西南地区的燃料。盐也产在杭州湾,运销西南地区。虽说水
则依赖西南地区的燃料。盐也产在杭州湾,运销西南地区。虽说水
运危险,水运仍极繁忙,但运费高昂,因为水上风险大,运输行必须付给工 厚礼。
厚礼。
这样,使国家遭受无形的损失,为数达到数百万贯之巨。
苏东坡就想在 知钱塘江
知钱塘江 形的
形的 协助之下,解决这个问题。新计划是想把通
协助之下,解决这个问题。新计划是想把通
往杭州的船运移到此危险地点上面的一条路。在苏东坡主持之下,拟定了一项计划,
需款十五万贯、员工三千,为时两年竣工。在此计划下,要将钱塘江引 一条八里
一条八里
长的新水道,水的 度足可供航运,要筑石堤一条,长两里又四分之一,在山下钻
度足可供航运,要筑石堤一条,长两里又四分之一,在山下钻
隧道六百一十尺长。不幸这项计划正在拟定中,他必须离开杭州。
同时,他也正在为另一项更迫切的问题忙得要命,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
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收成不佳。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涨到九十五文
一斗。幸而平仓里还有存粮,他又筹划到二十万石,卖出了十八万石,才算稳住米
价,在元信五年(一o九0)正月,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在那年春季多雨,看
来年成有望。农 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五月六
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五月六 ,杭州一带大雨滂
,杭州一带大雨滂
沦,多 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
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 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
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
 ,都能看出来,一已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
,都能看出来,一已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 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
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
的报告是该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 在划船抢救残存物
在划船抢救残存物
品。抢救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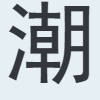 湿稻子还可烧
湿稻子还可烧 ,稻
,稻 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
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
虽然不需大才方可预知,苏东坡却在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常平仓制度远
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霍
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自七月开始,他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
七次,陈述实 ,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
,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
面五个叫“相度准备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 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
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
朝廷
 觉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背乎中国
觉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背乎中国 的习惯。若
的习惯。若 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
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
 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
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
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
但是他 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
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 ,这样不断存
,这样不断存
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与
饥民施舍,永远是 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
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
永远是气躁的。他指出来,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七五),没有 事先做何防备,
事先做何防备,
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须要拨出一百二十五万担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
五十万穷 饿死。除去
饿死。除去 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
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
失了三百二十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粮食就稳住
粮价,防止了灾 。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
。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
次严重。 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
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 减少,必须立即设法。
减少,必须立即设法。
奇怪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个 外,别
外,别 都是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
都是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
大怒。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 陈明新近的
陈明新近的 雨
雨
和水灾。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六个月以前,
他妻请拨给五万贯购买食米,杭州当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但邻省一
个名叶温举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钱一到,
 都想分润,但是
都想分润,但是
目前却无 肯陈报灾
肯陈报灾 。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
。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
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
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倘若他
的担心实属过虑,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
生, 民不会挨饿。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碱。苏东坡屡次写信有事与他会商,因为此
民不会挨饿。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碱。苏东坡屡次写信有事与他会商,因为此
事须与各地区配合协调。但是此 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他将因公外出,冬
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他将因公外出,冬 始可
始可
返杭。苏东坡在给他正在浙东为官的一位好友钱般的一封信里说:“虽子功旦夕到,
然此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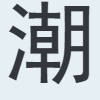 ,亦自佳事,试告公此意劝之,勿云
,亦自佳事,试告公此意劝之,勿云
仆言也。”在七月的报告中,苏东坡只请求拨米二十万石。那项计划也很简单。杭
州本为产米地区,每年只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杭州仍然很
殷实,能够付得出那个米额的价钱。如蒙允许保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缴同值的
绸缎银两。他只盼望朝廷准他们留下一部分充做皇粮的米,转到当地谷仓,也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