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面给各自的角色设计了 设和经历,以方便代
设和经历,以方便代 。
。
商迟到底更专业些:“只想这些大方向是不够的,你要想更快地融 进角色去,最好给他增加一点你自己的细节,比如根据他的
进角色去,最好给他增加一点你自己的细节,比如根据他的 格,猜测他会不会有一个无伤大雅的小癖好,拍摄的时候不用表现出来,但在你的心里,这个角色也许是个吃货,也许其实有点脸盲……你自己构想的这个
格,猜测他会不会有一个无伤大雅的小癖好,拍摄的时候不用表现出来,但在你的心里,这个角色也许是个吃货,也许其实有点脸盲……你自己构想的这个 物越具体越丰满,你就越像他,到最后,你
物越具体越丰满,你就越像他,到最后,你 他
他 的
的 ,你想他想的事,那时候就不用这么辛苦老师指导我们摆表
,你想他想的事,那时候就不用这么辛苦老师指导我们摆表 了,你摆的每个表
了,你摆的每个表 都是他。”
都是他。”
宁闲起愣愣地看着他。
他终于明白哪里不对了。
一个十四五岁就会关注学校啦啦队里哪个 生更好看、替腿最长的那个妹子惋惜没评上校花的小直男,就算再怎么珍惜朋友,又怎么会为了所谓的排名,来谈这种莫名其妙的恋
生更好看、替腿最长的那个妹子惋惜没评上校花的小直男,就算再怎么珍惜朋友,又怎么会为了所谓的排名,来谈这种莫名其妙的恋 呢?
呢?
他为了更好的营业,像一个开了上帝视角的编剧,置身事外,给自己和宁闲起设计了怎样的 设?添加了哪些细节?然后他又是怎样地融
设?添加了哪些细节?然后他又是怎样地融 进了自己写好的剧本,不断地完善,演到自己都信了的?
进了自己写好的剧本,不断地完善,演到自己都信了的?
宁闲起脑子一团 ,竭尽全力地回忆他们重逢以来的种种,想分清哪个是真正的商迟,可是根本一团
,竭尽全力地回忆他们重逢以来的种种,想分清哪个是真正的商迟,可是根本一团 麻。
麻。
他想,至少一个北京出生、伦敦长大的男孩儿,不会觉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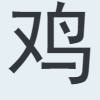 蛋羹该是甜的吧。
蛋羹该是甜的吧。
“商迟,”他艰难地开 ,“我觉得我找到感觉了,我先去拍完,然后下班以后我有话跟你说。”
,“我觉得我找到感觉了,我先去拍完,然后下班以后我有话跟你说。”
他在镜 前完美地表现出了导演要求的“悲伤中带着些许怜悯”。
前完美地表现出了导演要求的“悲伤中带着些许怜悯”。
因为他理应为自己感到悲伤,可是没有,他更多地在可怜自己唯一的朋友。
他一直以为商迟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却依旧乐观、开朗,还带着点恃宠而骄的小任 。
。
但万一,这个也是他演出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