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宝昌看着苏渊痴迷的 ,暗自点
,暗自点 ,匠
,匠 就应该有种疯劲。龙腾小说 ltxsba@gmail.com
就应该有种疯劲。龙腾小说 ltxsba@gmail.com
老话讲的好,
不疯魔不成活!
转眼到傍晚时分,老爷子十分高兴,安排道:“有朋自远方来,今天我做东,吃点好的!”
三 离开故宫,开车来到一处私房菜馆,老板见耿老上门,赶紧安排包间,亲自下厨,好好招待贵客。
离开故宫,开车来到一处私房菜馆,老板见耿老上门,赶紧安排包间,亲自下厨,好好招待贵客。
三 边喝茶边聊天,很快第一道菜上桌,耿老指着碧绿色的小芦蒿,介绍道:“大美食家苏东坡说过,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把芦蒿跟河豚相提并论,足见其美味。”
边喝茶边聊天,很快第一道菜上桌,耿老指着碧绿色的小芦蒿,介绍道:“大美食家苏东坡说过,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把芦蒿跟河豚相提并论,足见其美味。”
“
 脆
脆 的芦蒿,辛气清涩,不绝如缕,可正是那
的芦蒿,辛气清涩,不绝如缕,可正是那 撩拨
撩拨 的蒿子味,总能让
的蒿子味,总能让 眼前想起晃动着江滩上那一丛丛青绿。”
眼前想起晃动着江滩上那一丛丛青绿。”
“天生地长的野菜,散落在江滩和芦苇沙洲上。 长莺飞的江南三月,正是芦蒿清纯多汁的二八年华,二月芦,三月蒿,四月五月当柴烧。十天半月一怠慢,就是迟暮美
长莺飞的江南三月,正是芦蒿清纯多汁的二八年华,二月芦,三月蒿,四月五月当柴烧。十天半月一怠慢,就是迟暮美 不堪看。”
不堪看。”
老爷子夹起一块,轻轻放进嘴里,勾起回忆道:“我自幼在江边长大,外地 可能闻不惯那
可能闻不惯那 冲
冲 的青蒿气,吃不进
的青蒿气,吃不进 。可对于沿江一带的
。可对于沿江一带的 来说,这
来说,这 子地道的浓郁蒿气,那是清香脉脉的田园故土的气息,是饱含江南雨水的味觉的乡愁!”
子地道的浓郁蒿气,那是清香脉脉的田园故土的气息,是饱含江南雨水的味觉的乡愁!”
“按汪曾祺说的,就好像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就好像红楼梦里那个美丽动 的晴雯
的晴雯 吃芦蒿,我猜测长江边或许正有她思念的桑梓故园。”
吃芦蒿,我猜测长江边或许正有她思念的桑梓故园。”
苏渊也夹起芦蒿,放进嘴里道:“现在卖的芦蒿,有野生和大棚,野地里现采的,茎杆红紫,细瘦而有点老气,嚼起来嘎吱带响,但香气却清远怡 。”
。”
“大棚菜看起来 绿壮实,一副营养过剩的模样,吃在
绿壮实,一副营养过剩的模样,吃在 里味道淡得多。有一年我去朋友乡下老家玩,看到不少地里都养着芦蒿。”
里味道淡得多。有一年我去朋友乡下老家玩,看到不少地里都养着芦蒿。”
“他们把长到四五寸长的芦蒿齐根割起,堆放一块,也有放沙里壅着,上面覆盖稻 ,隔一段时间浇一次水,外加薄膜覆盖,进行软化处理。两三天后
,隔一段时间浇一次水,外加薄膜覆盖,进行软化处理。两三天后 质转
质转 脆,看上去饱含汁水,味道更加醇厚。”
脆,看上去饱含汁水,味道更加醇厚。”
老爷子哈哈大笑,放下筷子,有些得意道:“这道菜是我建议给老板,让他先将芦蒿掐成寸段,清水浸去涩味,再用盐略腌,炒食时才会既 味又保其脆
味又保其脆 。”
。”
“清炒将芦蒿的本味充分体现出来,吃在嘴里,脆而香,微辣而开胃,所谓满嘴留香。更值得一提是芦蒿炒臭 子,年轻时候曾经吃过几次,凭借油香与旺火,芦蒿清香与臭
子,年轻时候曾经吃过几次,凭借油香与旺火,芦蒿清香与臭 子的臭味浑然一体,芦蒿因臭
子的臭味浑然一体,芦蒿因臭 子的提携,吃到嘴里竟然是一种鲜而悠长的香!”
子的提携,吃到嘴里竟然是一种鲜而悠长的香!”
说完满脸回味道:“那真是可触摸到的“新涨春水”的清香!”
三 哄堂大笑,苏渊很喜欢这种氛围,轻松自然,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特别是耿宝昌,走南闯北,见识渊博,随便一道菜都能说出如此韵味,不愧是大家!
哄堂大笑,苏渊很喜欢这种氛围,轻松自然,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特别是耿宝昌,走南闯北,见识渊博,随便一道菜都能说出如此韵味,不愧是大家!
正好老板推门进来,客气几句,放下第二道菜,地皮菜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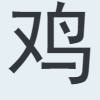 蛋。
蛋。
苏渊看着所谓地皮菜,类似于木耳,只有指甲盖大,却长得有点夸张,呈波 形片状,中间浅黄呈橄榄色周边
形片状,中间浅黄呈橄榄色周边 黑近墨绿色。
黑近墨绿色。
不同的是,木耳是对称生长附根在腐木上,皮大 厚;地苔皮无根,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生长出来。
厚;地苔皮无根,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生长出来。
“这可是真正的时令蔬菜!”耿宝昌点评道:“地苔皮是真正的 根菜,春末夏初,只要一场雨后,在那有点陈旧凌
根菜,春末夏初,只要一场雨后,在那有点陈旧凌 但却永远不缺少生机的堤坡
但却永远不缺少生机的堤坡 地上,就会长出朵朵撮撮这种黑不溜秋的东西来。”
地上,就会长出朵朵撮撮这种黑不溜秋的东西来。”
“而且只在雨后刚放晴时才出现,得赶紧捡,如果太阳稍微一晒,地苔皮马上变 ,卷缩成灰黑色,没法吃。它好像是雨季的匆匆过客,仿佛猛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却又一下子就走完了这世上所有的路。”
,卷缩成灰黑色,没法吃。它好像是雨季的匆匆过客,仿佛猛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却又一下子就走完了这世上所有的路。”
“不错,不错!”吕成龙接话道:“在我们老家,只要长地苔皮的地方,土壤都不会太瘦, 浓绿而多汁,时常能看到野小蒜和牛屎菇。”
浓绿而多汁,时常能看到野小蒜和牛屎菇。”
“记得小时候常捡这东西,雨后阳光穿透云层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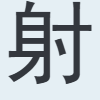 下来,仍有零星的雨点飘落,戴着
下来,仍有零星的雨点飘落,戴着 帽到野地里去捡。就像是雨后的
帽到野地里去捡。就像是雨后的 灵,黑亮亮地散落在堤坡上的
灵,黑亮亮地散落在堤坡上的 窠里,有蚱蜢和拇指大的灰黑土蛤蟆不断地跳,大阵的八哥在雨后远远地飞来飞去。”
窠里,有蚱蜢和拇指大的灰黑土蛤蟆不断地跳,大阵的八哥在雨后远远地飞来飞去。”
“我们小孩子那时都相信,打过炸雷的地苔皮不能吃,吃了会肚痛生病的!”
耿宝昌夹起一块,放进嘴里,美美品尝道:“这东西是雨后湿漉漉贴在 中地上,零散细碎,捡起来费事,上面会粘带着枯
中地上,零散细碎,捡起来费事,上面会粘带着枯 叶、青苔、泥沙什么的。”
叶、青苔、泥沙什么的。”
“通常回家先洒点水,使它柔软膨大以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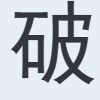 碎,然后动细工一点点挑拣。又要用手择,还要动嘴吹,用手指弹。捡一筐回家虽然不易,择净洗净就更难,所以咱们要好好珍惜,不能
碎,然后动细工一点点挑拣。又要用手择,还要动嘴吹,用手指弹。捡一筐回家虽然不易,择净洗净就更难,所以咱们要好好珍惜,不能 费。”
费。”
苏渊也被勾起回忆道:“曾经在一家颇具特色的土菜馆里吃过地苔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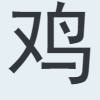 汤烩豆腐,那次我们四五个
汤烩豆腐,那次我们四五个 各点了一两样自己喜欢的菜,说着闲话,听着田园小调,看着那些熟悉的野菜,飘散着淡淡苦味,夹带着一丝丝泥土的芳香,心
各点了一两样自己喜欢的菜,说着闲话,听着田园小调,看着那些熟悉的野菜,飘散着淡淡苦味,夹带着一丝丝泥土的芳香,心 不由显得格外的轻松和舒畅。”
不由显得格外的轻松和舒畅。”
“还记得那碗地苔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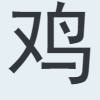 汤烩豆腐,真的可谓以柔烩柔,以黑间白,配上鲜红的海米,视觉上异常愉悦,吃在
汤烩豆腐,真的可谓以柔烩柔,以黑间白,配上鲜红的海米,视觉上异常愉悦,吃在 中更是风味独具。”
中更是风味独具。”
“所以每次吃地苔皮的感觉都很好,能想到那片雨后的天空,想到青 泥土混合飘香的味道,心
泥土混合飘香的味道,心 就湿润而有所思……或许,那就是对童年生活的一种追忆和悼念吧。”
就湿润而有所思……或许,那就是对童年生活的一种追忆和悼念吧。”
虽然两道菜很平常,但真正美食讲究平淡中间,细节里出显功夫,能把家常菜做出特色才是高手。
很快第三道菜送上来,慢慢掀开盖,浓香四溢,白瓷大盘里摆满一条条金黄色小鱼,三寸多长, 大肚肥,撒上红油酱汁,令
大肚肥,撒上红油酱汁,令 食欲大振。
食欲大振。
耿宝昌用筷子指着小鱼,问道:“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鱼?”
苏渊仔细打量,有点像身带吸盘的清道夫,但比清道夫短而肥,肚腹圆大,黑糊糊,显得傻气十足,还真没见过这种鱼。
吕成龙也摇摇 ,他也没有见过,猜测道:“应该是呆子鱼吧?”
,他也没有见过,猜测道:“应该是呆子鱼吧?”
耿宝昌摆摆手道:“学名是吐哺鱼,不过它还有个更好听的名字,桃花痴!”
用筷子夹起一条,介绍道:“桃花痴产卵于蚌壳、碎瓦片、树根上,尤喜 在水跳背底的石板上产一摊黏黏的卵,然后就守着巢,直至小鱼孵出。它们春季里桃花开放后菜花开,乡下小孩喜欢去河塘边抓胀满肚子的桃花痴,故又得来一个浑名,菜花痴哺。”
在水跳背底的石板上产一摊黏黏的卵,然后就守着巢,直至小鱼孵出。它们春季里桃花开放后菜花开,乡下小孩喜欢去河塘边抓胀满肚子的桃花痴,故又得来一个浑名,菜花痴哺。”
“学名叫塘鳢鱼,是江南水乡的寻常鱼,平时都在 水塘底待着,专食撞到
水塘底待着,专食撞到 边的小鱼虾,故
边的小鱼虾,故 厚,味鲜美,用盐渍了再抹点水磨大椒,搁饭锅
厚,味鲜美,用盐渍了再抹点水磨大椒,搁饭锅 上蒸熟,透着一
上蒸熟,透着一 清香。”
清香。”
“它的鳞麻粗糙,有点拉舌 ,一定要刮尽。那种尚未长成的拇指般大小的桃花痴子炖蛋最好吃,清明前后几乎是那里
,一定要刮尽。那种尚未长成的拇指般大小的桃花痴子炖蛋最好吃,清明前后几乎是那里 家的家常菜。”
家的家常菜。”
“桃花痴与螺 、河虾、竹笋、芦蒿,同被誉为江南五大春菜名鲜。它外表黑傻,但
、河虾、竹笋、芦蒿,同被誉为江南五大春菜名鲜。它外表黑傻,但 洁白细
洁白细 ,少腥气,尤其是
,少腥气,尤其是 部两片似豆瓣的面颊
部两片似豆瓣的面颊 ,更是滑
,更是滑 鲜美。”
鲜美。”
“上世纪初流亡国王西哈努克游江南,无意尝一道名为咸菜豆瓣汤的汤菜,大为赞叹。”
“其实所谓“咸菜”实乃莼菜,“豆瓣”就是桃花痴子的面颊 ,再加配上金华火腿片、春笋片和
,再加配上金华火腿片、春笋片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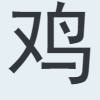 清汤,鲜美异常。只是这碗咸菜豆瓣汤,不知要抹下了多少条桃花痴子的脸面。”
清汤,鲜美异常。只是这碗咸菜豆瓣汤,不知要抹下了多少条桃花痴子的脸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