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所受到
的启发挖掘出来并运用到《恶魔孽种》中去。他放弃了以往用蓝色化学原料贴在窗
上使光线更显自然的方法,而采用近光,使背向光移动的 物被罩在光圈中给
物被罩在光圈中给
以幻相,就好像“上帝之光”穿过云烟和尘埃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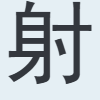 下来。斯皮尔伯格后来在许多影
下来。斯皮尔伯格后来在许多影
片中都运用过这种手法。
《追杀》于1971年11月13 公演,它的艺术表现力给了那些对斯皮尔伯格以前
公演,它的艺术表现力给了那些对斯皮尔伯格以前
的电视作品不感兴趣的朋友们很 的印象。乔治。卢卡斯回忆说:
的印象。乔治。卢卡斯回忆说:
虽然我早在60年代初就在电影节上认识了史蒂文,但直到1971年某个
时候我才真正注意他。那时我正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聚会上,电
视里正在播放《追杀》。我早就对这部片子感到好奇,于是我想我该溜上
楼去看上10分钟。可我一看上就再也无法离开……我想,这家伙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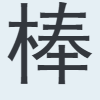 ,我
,我
该好好了解了解他。
给《追杀》这片子下定义是个智力游戏。多数美国评论家把它看作是流行社会
学的产物,和用来反对某种令他反感的事物的武器,如:机能障碍、 神错
神错 、污
、污
染。
对欧洲 来说,他们更愿意探究一部片子的艺术
来说,他们更愿意探究一部片子的艺术 而不是它的象征
而不是它的象征 。为英国
。为英国
电影杂志《观察与评论》工作的汤姆。梅思说:“有些冒昧地说,《追杀》向 们
们
展示出一个存在主义者对金石(使其他金属也变成金子的不存在的东西)始终不渝
又自命不凡地的追求,即追求那些所谓十全十美、绝对正确、怪异的和自我满足的
东西。”梅思的确注意到了后来成为斯皮尔伯格影片风格的两个显著标志。一个是
带有典型的中世纪骑士风格的特征,这从他的影片《印第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圣
战》中再次表现出来。《追杀》中的卡车首先在曼的眼前来了个急转弯,就像“骑
士甩掉了手套”一般地宣战,然后“在追击者与被追击者之间展开了车战,卡车像
龙一样施着笨重的车身缓缓前行,闪闪发光的普利茅斯小汽车也像个令 同
同 的身
的身
着盔甲的骑士在奋勇向前”,斯皮尔伯格后来承认他把这一幕看成是一个男 在同
在同
一个商速路上的骑士决斗。斯皮尔伯格电影的另外一个标志,与前者截然相反,是
带有典型的脱离现实世界的唯我主义的风格特征。曼和卡车司机几乎是为了对抗才
存在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表现他们的特,就像斯皮尔伯格后来在拍《大白鲨》
时,为捕捉鲨鱼的 安排的行为,在拍《第三类接触》以及在拍《印地安那琼斯》
安排的行为,在拍《第三类接触》以及在拍《印地安那琼斯》
时为罗伊·奈瑞安排的行为一样。
《追杀》提高了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公司的身价,尤其是他在技术 员中的身价,
员中的身价,
这些 多数都与环球公司有合同,为了
多数都与环球公司有合同,为了 后好找工作的原因,他们都希望找个能给
后好找工作的原因,他们都希望找个能给
他们带来些名气的 合作。他们不是不在乎评论家说些什么,而是更在乎是否能被
合作。他们不是不在乎评论家说些什么,而是更在乎是否能被
这个孩子好好关照,以便使他们的收 看起来还不错。《追杀》公演两星期后,这
看起来还不错。《追杀》公演两星期后,这
公司从前的导演兼制片 汤姆·劳夫林就与《追杀》的摄影师杰克·马塔签了合同,
汤姆·劳夫林就与《追杀》的摄影师杰克·马塔签了合同,
让他去拍摄使他很成功的系列片《比利·杰克》(Billy Jack)。剪编弗朗克·毛里
斯发现,请求让他剪片子的 越来越多。助理导演吉姆·法够被克林特·伊斯特伍
越来越多。助理导演吉姆·法够被克林特·伊斯特伍
德挑走做了他片子的导演。诸如此类之事,围绕着斯皮尔伯格在继续发生。当斯皮
尔伯格1985年为环球公司拍完电视系列剧后,作曲家比利·戈顿伯格就开始为《惊
奇故事》作曲了。许多参加了《恶魔孽种》拍摄工作的 都参加了斯皮尔伯格以后
都参加了斯皮尔伯格以后
的拍片工作,包括摄影师比尔· 特勒和卡尔·离特雷伯,还有在这部影片中演小
特勒和卡尔·离特雷伯,还有在这部影片中演小
角色的那些来自长滩的朋友,以及后来的和他一道合作编写《大白鲨》的朋友。
环球公司收到了许多来自其他电影厂邀请斯皮尔伯格去拍电影的请求。不幸的
是,公司一概拒绝了这些请求。莱文森和林克马上借此机会抓住斯皮尔伯格让他再
拍一部试播片。看过《传道》(Mission)之后,观众都希望马丁·兰多和
 拉这对
拉这对
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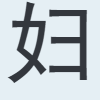 再度于《难以完成的使命》(Mission Impossible)中出演记者保尔·塞威格和
再度于《难以完成的使命》(Mission Impossible)中出演记者保尔·塞威格和
他的妻子。无论斯皮尔伯格提过多少要求拍影院影片的抗议,辛伯格仍不改变他的
主意。尽管后来是由斯皮尔伯格的老朋友 瑞·舒力文在这部片子中扮演了敲榨记
瑞·舒力文在这部片子中扮演了敲榨记
者赛威格一家的法官,但这次经历并没有让斯皮尔伯格感到光彩。
他瞎位乎了一阵子,把从前的片名《监视塞威格报告的 》做了修改,1971年,
》做了修改,1971年,
它以《塞威格》的片名上演了。评论家对此各执一说。斯皮尔伯格后来说,这是他
惟一一次被 强迫去拍的电影,即使如此,这也不足以让斯皮尔伯格违背公众的意
强迫去拍的电影,即使如此,这也不足以让斯皮尔伯格违背公众的意
愿而按自己的意愿去拍片子。
在给《追杀》又加了9分钟的内容后,环球公司把它拿去参加了5月份的法国嘎
纳电影节,去给欧洲电影发行充当一个小小开场白。斯皮尔伯格也去了,这是他第
一次离开美国的旅行。在 黎的一个雨天的下午。他的一位朋友拉着他穿过凯旋门,
黎的一个雨天的下午。他的一位朋友拉着他穿过凯旋门,
斯皮尔伯格穿着喇叭型中仔裤、方 皮靴,细横条衬衫,紧身夹克,像个衣着不整
皮靴,细横条衬衫,紧身夹克,像个衣着不整
的小男孩儿似地跟在他的朋友身后。斯皮尔伯格崇敬地环顾四周, 黎!7月,斯皮
黎!7月,斯皮
尔伯格又到了罗马,环球公司住罗马的工作 员安排斯皮尔伯格与弗德里克·弗里
员安排斯皮尔伯格与弗德里克·弗里
尼共进午餐。让斯皮尔伯格感到吃惊的是,这位先生带他来的这家美国风味餐馆里
的 ,对弗里尼和弗里尼的客
,对弗里尼和弗里尼的客 们的态度不同,他们不让他坐在他的客
们的态度不同,他们不让他坐在他的客 们旁边,
们旁边,
只因为他没有系领带。弗里尼怒气冲冲地走出饭店,扭 说道:“好吧,我们现在
说道:“好吧,我们现在
去意大利餐馆。”
欧洲充斥着浓厚学者气息的氛围并不让 感到惬意。在罗马,左翼评论家
感到惬意。在罗马,左翼评论家 迫
迫
斯皮尔伯格同意他们在文章中对《追杀》所作的比喻:卡车象征着工 阶级,小汽
阶级,小汽
车象征着资产阶级,这是一场工 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较量。当斯皮尔伯格表示不同
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较量。当斯皮尔伯格表示不同
意他们的观时,他们中有4个 吵嚷着离去。斯皮尔伯格再也不打算卷
吵嚷着离去。斯皮尔伯格再也不打算卷 这类政治
这类政治
活动了。作为一个大众制片 ,他不能接受“电影是政治的化身”的观。这等于
,他不能接受“电影是政治的化身”的观。这等于
是把电影中的某个 说成是阶级力量。斯皮尔伯格曾在嘎纳节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
说成是阶级力量。斯皮尔伯格曾在嘎纳节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
者说:“这些相信‘化身’理论的导演们等不到老就会得血栓。因为你不可能同时
弹奏所有的乐器。”
斯皮尔伯格接受了 们对《追杀》的所有恭维,甚至包括那些听起来有些荒谬
们对《追杀》的所有恭维,甚至包括那些听起来有些荒谬
的恭维。有 说《追杀》是一份对“机器的起诉书”,这是十分恰如其分的,因为
说《追杀》是一份对“机器的起诉书”,这是十分恰如其分的,因为
斯皮尔伯格太热衷于用机器 纵
纵 们的视觉
们的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