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意没等实施,就被警觉的四卿联手 碎。四卿抄起武器,把自己的国君打跑了。(只有在犯上的时候,四家才是异常齐心协力啊)。
碎。四卿抄起武器,把自己的国君打跑了。(只有在犯上的时候,四家才是异常齐心协力啊)。
可怜的晋出公死在出奔的道路上。智伯又立了一个晋哀公(唉,这个可怜的名字啊,凑活着对付几年吧)。
智伯这些卿大夫家族自有封地和封地上的军队与粮食,势力积累了上百年,以至于可以凌 国君。
国君。
由于是他带 分了范、中行的地,国君又是他一手扶立的,智伯感觉到了自己伟大得一塌糊涂,而赵、魏、韩三个胆小鬼,纯粹是寄活在自己卵翼下,跟着自己沾光。所以,智伯就非常想给这三个吃白饭的家伙以脸色看。
分了范、中行的地,国君又是他一手扶立的,智伯感觉到了自己伟大得一塌糊涂,而赵、魏、韩三个胆小鬼,纯粹是寄活在自己卵翼下,跟着自己沾光。所以,智伯就非常想给这三个吃白饭的家伙以脸色看。
次年,智伯跟魏桓子(跟随重耳长征过的九袋长老魏仇的六世孙,魏家掌门 )、韩康子(司马韩厥的三世孙,韩家掌门
)、韩康子(司马韩厥的三世孙,韩家掌门 )一起在蓝台喝酒。席间,智瑶不仅戏弄了韩康子,还污辱了韩的家臣“段规”(具体细节不详,不排除
)一起在蓝台喝酒。席间,智瑶不仅戏弄了韩康子,还污辱了韩的家臣“段规”(具体细节不详,不排除 身污辱——比如喝尿的可能)。
身污辱——比如喝尿的可能)。
智伯的家臣比较谨慎,进谏说:“主公应该防备他们报复!”
智伯哈哈大笑,豪迈地说:“我不报复他就是好事了,这两个吃白饭的家伙。”
家臣说:“从前,隙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被 灭掉,都是因为他们招惹了别
灭掉,都是因为他们招惹了别 的怨恨,借机挑拨陷害,导致家族败亡(家族大了,就招风,成为怨府)。马蜂、蚊子虽小,也会咬
的怨恨,借机挑拨陷害,导致家族败亡(家族大了,就招风,成为怨府)。马蜂、蚊子虽小,也会咬 啊。”
啊。”
三年后,智伯继续找茬,他派 对三家说:“咱们的国君太可怜了,你们都看见了。(是啊,要不怎么叫晋哀公呢)。咱们身为上卿,都应该忠君
对三家说:“咱们的国君太可怜了,你们都看见了。(是啊,要不怎么叫晋哀公呢)。咱们身为上卿,都应该忠君 国。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大河不满小河怎么满。所以,每
国。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大河不满小河怎么满。所以,每 都拿出些地方来,赞助给国君。”
都拿出些地方来,赞助给国君。”
韩康子最窝囊,实力排在四卿之末,赶紧跟家臣商量,不拿出来吧,怕智伯找着了借 ,以国君名义,正好来打。拿出来吧,白吃亏。家臣说:“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亏了我一个,还有后来
,以国君名义,正好来打。拿出来吧,白吃亏。家臣说:“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亏了我一个,还有后来 。等他智伯吃惯了便宜,尝甜
。等他智伯吃惯了便宜,尝甜 上瘾,就还会跟别
上瘾,就还会跟别 也伸手要。别
也伸手要。别 不买他的帐,到时候打起来,咱就有戏瞧了。”耶,这主意不错,就当花钱买张戏票吧。
不买他的帐,到时候打起来,咱就有戏瞧了。”耶,这主意不错,就当花钱买张戏票吧。
于是韩康子拿出文书,划出一个封邑(万户
 ),盖上铜玺的章,送给智伯。智伯接了,算你小子还不傻,然后把黑手又往魏桓子面前一伸:“快,该你了。”
),盖上铜玺的章,送给智伯。智伯接了,算你小子还不傻,然后把黑手又往魏桓子面前一伸:“快,该你了。”
魏桓子很想拒绝,家臣害怕了,劝说道:“ 家韩家给了,咱要是不给,
家韩家给了,咱要是不给, 等着智氏来打,被韩家看戏。咱也给吧。《周书》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嘛。”
等着智氏来打,被韩家看戏。咱也给吧。《周书》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嘛。”
于是,因此,魏桓子也盖了个戳, 出一万家户
出一万家户 。
。
智伯看了看清单,基本满意了,但就差赵无恤了。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个硬骨 。
。
赵无恤是个“守雌主义者”,这固然是由于他是姨娘生的,从小自卑。同时,赵家 的
的
 ,从赵衰、赵盾、赵朔、赵武一脉下来,也都比较文质,心慈面软,类似大宋朝“偃武修文”的赵姓皇帝。这种家族
,从赵衰、赵盾、赵朔、赵武一脉下来,也都比较文质,心慈面软,类似大宋朝“偃武修文”的赵姓皇帝。这种家族 格刚好跟智氏的粗鲁桀骜相映成趣。
格刚好跟智氏的粗鲁桀骜相映成趣。
但是,赵无恤外边虽柔,内里却刚,他不准备再伏首贴耳,毅然回绝智伯的使者。他说:“土地是先 的产业,哪能随意送
的产业,哪能随意送 ?”
?”
使者一走,赵无恤赶紧把僚属“张孟谈”叫来:“智伯移兵打我的话,怎么办?以赵氏的力量,跟他对抗,众寡悬殊,孤木难持啊。”
张孟谈是史载第二个姓张的 (上一个是晋国的张老),张孟谈说:“晋阳是董安于修建的,城垣坚固,仓廪充实。尹铎治理那里,宽恤有恩,政教清明,不把老百姓当作蚕茧来抽丝,而是实行
(上一个是晋国的张老),张孟谈说:“晋阳是董安于修建的,城垣坚固,仓廪充实。尹铎治理那里,宽恤有恩,政教清明,不把老百姓当作蚕茧来抽丝,而是实行 为减税。所以
为减税。所以 们愿意效死。”
们愿意效死。”
“对啊,我爹在的时候,也嘱咐我,如果出现三长两短,紧急 况,不管相离多远,也要跑到晋阳去。那是我爹在边境上新修的一座坚城。”
况,不管相离多远,也要跑到晋阳去。那是我爹在边境上新修的一座坚城。”
于是,赵无恤收拾东西,避敌锋芒,率军北趋400里,退保晋阳。《战国策》中有这么一句话,赵无恤“令车骑先至晋阳”。这标志着骑兵的出现,但还是和车兵混合编制的,尚未成为独立的兵种。
郊外的空气真好啊,赵无恤一边欣赏着盆地山景,一边在城 检查工事。晋阳城的一个特就是“固”。城高池
检查工事。晋阳城的一个特就是“固”。城高池 、宫苑壮丽,坚厚的城墙以夯土打造,中间还加固木桩、石础。晋阳
、宫苑壮丽,坚厚的城墙以夯土打造,中间还加固木桩、石础。晋阳 心也很固,百姓心无二志,不会哗变。但是,赵无恤担心城里的弓箭、武器不够用,一旦打起持久战来,就会弹尽粮绝,光有个城墙有什么用呢。
心也很固,百姓心无二志,不会哗变。但是,赵无恤担心城里的弓箭、武器不够用,一旦打起持久战来,就会弹尽粮绝,光有个城墙有什么用呢。
张孟谈说:“当年董安于修筑晋阳城,用荻蒿主竿做墙骨,用铜柱替代木柱。咱把它挖出来,正好用来制造箭杆,把铜柱熔化了,就可以造武器。”董安于(董狐的后代,晋阳的缔造者和殉身者)的 谋远虑,继上次拯救了赵简子之后(被范氏、中行氏追赶至此),又要护住赵无恤了。
谋远虑,继上次拯救了赵简子之后(被范氏、中行氏追赶至此),又要护住赵无恤了。
晋阳这个地方,是个天生的“战地”和“攻守之场”,最招 来打了。在后来的1400年中,一直是万
来打了。在后来的1400年中,一直是万 鏖战的中心。
鏖战的中心。
从汉朝起,这里一直是抵抗匈 等异族的前线堡垒,西晋末年,刘琨喋血保卫晋阳,抵御匈
等异族的前线堡垒,西晋末年,刘琨喋血保卫晋阳,抵御匈
 侵,坚持长达 9年。刘琨败死后,五胡彻底
侵,坚持长达 9年。刘琨败死后,五胡彻底 华,整个北方群魔
华,整个北方群魔 舞,
舞, 民涂炭。
民涂炭。
隋朝以后,这里向内地的战略意义也体现出来了,被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誉为“龙兴之地”。他们爷俩就是从晋阳发家,起兵反隋,不管抵御突厥、政府军还是农民军,都是依托这里。什么都可以丢,但晋阳不能丢。李世民号称“晋阳公子”。
唐朝安史之 ,这里又成为政府军与叛军的争夺场。政府军大将“李光弼”被围于此,凭借坚固的城池,挖掘地道出击,抛石机轰砸,坚守晋阳五十多天,歼灭敌军“史思明”部7万余
,这里又成为政府军与叛军的争夺场。政府军大将“李光弼”被围于此,凭借坚固的城池,挖掘地道出击,抛石机轰砸,坚守晋阳五十多天,歼灭敌军“史思明”部7万余 ,最终解围,扭转全国战局。
,最终解围,扭转全国战局。
唐末的 世,五代十国,这里又出了好几个“绿林皇帝”,走马灯似地
世,五代十国,这里又出了好几个“绿林皇帝”,走马灯似地 换,依托“龙城”晋阳,向西鞭伐长安,向南横扫中原(洛阳)。
换,依托“龙城”晋阳,向西鞭伐长安,向南横扫中原(洛阳)。
到了宋初,赵光胤、赵光义两个皇帝先后亲征这里。前者顿挫无功,折锐而返,后者则动用现代化攻城器械:以负重高达九十斤的抛石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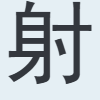 程达三里的弩箭猛轰晋阳,还出现了集束发
程达三里的弩箭猛轰晋阳,还出现了集束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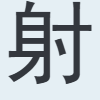 的弩箭,火药兵器也开始应用。赵光义亲冒矢石督战,异常艰苦残烈。守城的是北汉主“刘继元”,坚守五个月之久,可见该城之雄坚。
的弩箭,火药兵器也开始应用。赵光义亲冒矢石督战,异常艰苦残烈。守城的是北汉主“刘继元”,坚守五个月之久,可见该城之雄坚。
当时,宋军的抛石机 夜轰击晋阳城垣,以至于城墙伤痕累累,城
夜轰击晋阳城垣,以至于城墙伤痕累累,城 几乎没有完整堞
几乎没有完整堞 。好几万名弓弩手列阵于城下,一个多月时间,昼夜不息向城中
。好几万名弓弩手列阵于城下,一个多月时间,昼夜不息向城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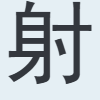 击,箭雨如飞腾的蝗虫避
击,箭雨如飞腾的蝗虫避 ,压向晋阳。一次拔付的几百万支箭矢在片刻之间往往
,压向晋阳。一次拔付的几百万支箭矢在片刻之间往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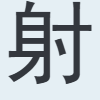 尽。城
尽。城 飞集的箭羽如同刺猬毛刺一般,新箭都没有落脚地方。更多密集的流箭飞越城
飞集的箭羽如同刺猬毛刺一般,新箭都没有落脚地方。更多密集的流箭飞越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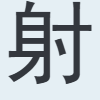
 城内,仅刘继元派
城内,仅刘继元派 以十钱一支的价格向市民回收,就得到一百余万支。
以十钱一支的价格向市民回收,就得到一百余万支。
中国的守城史,未见如此壮观惨烈的。最后,五个月后,城内粮尽援绝,方才投降。余恨未销的宋太宗下令摧毁晋阳,火烧水灌,彻底拉倒。这座千年名城,从此画上一个光辉的句号,宣告正寝。(当初,建于赵姓 手里,也毁在赵姓
手里,也毁在赵姓 手里。生于泥土,归于泥土。当然这中间经过不断再造,最盛的时候分做三城,首尾24个城门)。
手里。生于泥土,归于泥土。当然这中间经过不断再造,最盛的时候分做三城,首尾24个城门)。
公元前454年,晋四卿的老大——智伯先生,要想攻打的,就是这么一个有着未来光辉战绩、傲 历史的城池——真够智伯受的!他的攻城武器远远比不上宋朝呢,怎么办?智伯的时代也有抛石机,但力量幼稚,只算花拳绣腿而已。智伯咬着牙,驱赶智、魏、韩联军,仰攻三个月,昼夜激战,毫无进展。然后改为围城消耗战,一围就是一年多(一说三年),晋阳城稳丝不动。
历史的城池——真够智伯受的!他的攻城武器远远比不上宋朝呢,怎么办?智伯的时代也有抛石机,但力量幼稚,只算花拳绣腿而已。智伯咬着牙,驱赶智、魏、韩联军,仰攻三个月,昼夜激战,毫无进展。然后改为围城消耗战,一围就是一年多(一说三年),晋阳城稳丝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