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 咏诗。
咏诗。
今 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
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 皮。
皮。
苏夫 听见这首诗,不由得
听见这首诗,不由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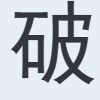 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
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
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
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 京。太守官邸的
京。太守官邸的 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
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
躲藏藏。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官差
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
逮捕太守犹如捕盗。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
有 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
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
他想跳 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
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
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 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
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
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闭跳 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
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
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
的通信和手稿。家里 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
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 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
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
书信和别的文件。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
 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
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
东西胡 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兵丁走后,
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兵丁走后,
 们气冲冲的说:“这
们气冲冲的说:“这
都是写书招惹的。他 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
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 都吓死了。”然后焚烧他的手稿,
都吓死了。”然后焚烧他的手稿,
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 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
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 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
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
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
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 的习惯。
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
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
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 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
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
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 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
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
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 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
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
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词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 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
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
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
恩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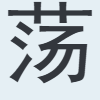 ,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
,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
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
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 还
还
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 写
写
的片纸只字呈 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
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
手中。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
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幸亏诗 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
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
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此书包括四件弹劾
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 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陆游勤于写
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陆游勤于写 记,对
记,对
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 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
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
的。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北宋在靖康元年(—一二六)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
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
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
 请求为先
请求为先 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
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 只答应
只答应 出
出
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
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 流传下来
流传下来
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
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
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
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
中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
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
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 恨亲
恨亲 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
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
法。
舒禀在表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龛然,
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 固不为少……然包
固不为少……然包
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 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
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 所言,无一不以
所言,无一不以
讥诗为主。……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轼
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
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悻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且 道所立者、以有义而无逃于天地
道所立者、以有义而无逃于天地
之间者,莫如君臣。轼之所为忍出于此,其能知有君臣之义乎?为 臣者苟能充无
臣者苟能充无
义之心往之以为利,则其恶无所不至矣……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有
而已。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 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另一御史的弹劾表里,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
为张氏园写了一篇记。在此一篇文章里,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那位
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 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
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
不道,他说:“天下之 ,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
,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
